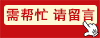外婆的腌菜壇
整理老屋時,我在廚房角落發現了那只青釉腌菜壇。壇口結著陳年的鹽霜,壇底一圈經年的油漬,像被歲月暈染的水墨畫。輕輕揭開竹編蓋子,咸香的氣息裹挾著陽光的溫度撲面而來,恍惚間,我又看見外婆踮著腳往壇子里撒鹽的模樣。
青釉壇里的晨光
每天天還沒亮,外婆就會踩著露水去菜園。她的藍布圍裙兜著新摘的蘿卜,根須上還沾著夜露。“要趁太陽沒出來,菜心才脆生。”她總說這話時,手指在青釉壇的紋路間摩挲,仿佛在確認壇子里沉睡的時光。腌菜時,外婆會把粗鹽在鐵鍋里炒得噼啪作響。“這樣鹽才不生蟲。”她的銅頂針在晨光中泛著溫潤的光,將蘿卜條碼進壇子的動作像在完成某種儀式。我蹲在旁邊數她白發,發現每一根都沾著鹽粒般的霜花。壇口的封泥是用面粉和水調成的,外婆封壇時總要用竹片在鹽水里劃個十字:“這樣咸淡才勻。”有時她會往壇沿倒半碗清水,看氣泡咕嚕嚕地冒上來,仿佛在確認壇子里的生命是否安好。

時光發酵的味道
清明前后,壇子里的酸豆角開始蘇醒。外婆掀開蓋子的瞬間,酸味像調皮的孩子竄出來,逗得我直打噴嚏。她用長柄木勺攪動鹽水,褐色的豆角在琥珀色的液體里舒展,如同游動的精靈。“嘗嘗看。”外婆總會用竹夾子夾起一根,我咬下的瞬間,酸脆的口感在舌尖炸開,混著微微的辣味。她笑著替我擦去嘴角的鹽水:“這是去年重陽曬的辣椒,辣得人心里亮堂。”最難忘的是冬天的腌蘿卜。外婆把白蘿卜切成薄片,鋪在竹匾里曬太陽。霜白的蘿卜片漸漸蜷縮,像被抽走水分的月亮。當它們與壇子里的老鹽水重逢,便會在黑暗中完成一場華麗的蛻變。
走不出的咸香
去年冬天,我在異地的餐館吃到腌黃瓜。那味道寡淡得像被稀釋的回憶,黃瓜片生硬地浮在醋水里,毫無生氣。結賬時,我盯著玻璃罐里的腌菜發呆,老板娘誤會我想買,“這是工廠批量做的,哪有家里的香?”這句話讓我想起外婆臨終前的場景。她瘦得像片風干的菜葉,卻執意要教我腌菜:“壇沿水要每天換,不然會臭……”她的手在被子上摸索,仿佛還在碼放那些脆生生的蘿卜條。 如今我站在老屋的廚房里,用外婆留下的木勺攪動鹽水。窗外的梧桐葉沙沙作響,恍惚間又聽見她喊我:“妮子,快來嘗嘗咸淡。”壇子里的氣泡依然在冒,只是這次,我嘗到了時光沉淀的甜。走出老屋時,暮色正漫過門檻。手里的腌菜罐輕輕搖晃,罐底的鹽粒發出細碎的聲響,像外婆在絮絮叨叨地說著那些被腌漬的歲月。咸香的氣息漫過街角的梧桐樹,漫過童年的石板路,漫過所有回不去的舊時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