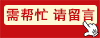愛晚亭·楓紅霞影
█方富貴 劉滿元 彭樹青
11月29日的傍晚,幾位戰友相約于“愛晚亭”看岳麓山紅楓。這里的楓葉紅得晚些,特別是日影西斜、天地將合之際,賞楓別有一番風味。

暮色漸沉,初冬的夕陽余暉將天邊染成一片金橙,宛如一幅靜謐而深邃的水墨畫。那座歷經百年風雨的“愛晚亭”,靜靜佇立在山腰間,迎著深沉的楓葉,訴說著歲月的變遷與人世的悲歡。
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余脈,自古以來便是文人墨客吟詩作賦的勝地。山中的愛晚亭,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,由岳麓書院山長羅典所建,最初名為“紅葉亭”,后因唐代詩人杜牧那首膾炙人口的《山行》“停車坐愛楓林晚”,遂易名“愛晚亭”,以表達對晚秋楓林的摯愛,也映射了對人生暮景的深沉體悟。自此,“愛晚亭”便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一座古典亭子,更升華為湖湘文脈的圖騰,凝聚著歷史的厚重與文人的風骨。
微風徐起,層林盡染,岳麓山的楓葉終于換上了火紅的盛裝。遠望之,漫山遍野似流霞傾瀉,如烈火燎原;近觀之,片片紅葉脈絡清晰如畫,在余暉中,或明艷,或深邃。漫步其間,微風拂面,落葉鋪地,古亭與紅葉相映成趣,將初冬的浪漫與生命的熱烈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站在亭前,但見亭身方正,重檐八柱,琉璃碧瓦在夕照下流轉著溫潤光澤。飛檐高翹,仿佛輕盈欲飛,直欲乘風攬月。亭內懸掛著毛澤東手書的《沁園春·長沙》橫匾,那墨跡遒勁如龍蛇飛動,將改天換地的革命豪情與源遠流長的湖湘文脈熔于一爐。亭柱楹聯鐫刻:“山徑晚紅舒,五百夭桃新種得;峽云深翠滴,一雙馴鶴待籠來。”寥寥數語,便將山水之靈與人文之雅,在這方寸之地氤氳交融,引人神馳千古。
夕陽的余暉,執著地穿過密匝的楓葉縫隙,灑在亭檐飛檐上,斑駁光影搖曳生姿。山巒浸透深紅,紅葉愈發絢爛。靜立期間,敬畏油生:天地浩瀚無垠,人生白駒過隙,唯有在這片紅色的海洋中,感受到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珍貴。
戰友們圍坐亭中,笑語低徊。鬢角染霜的老首長,目光深邃,望向那最沉穩的深紅楓葉,聲音溫和而篤定:“看這楓葉,紅得晚一些,但更顯得沉郁、醇厚,就像人生的晚年,越發懂得珍惜與感悟。”話語間,是對過往的珍重,也是對未來的從容。身旁稍顯年輕的戰友頷首:“是啊,我們這一代,承前啟后,肩上的擔子不輕。便如這楓葉,在有限光陰中,必燃盡絢爛。”言語里,是責任的沉甸,更是理想的熾熱。

此情此景,李商隱“夕陽無限好,只是近黃昏”的喟嘆縈繞我心頭,而風韻卓然的女戰友輕吟:“霜葉紅于二月花”,聲如裂帛,刺破暮色,既禮贊生命的韌性,更叩問存在的意義。
此刻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愛情,那個曾經的風華絕代的故事。
愛晚亭畔,青年的毛澤東,曾無數次登高望遠,指點江山,激揚文字。岳麓山的楓紅,見證了他“問蒼茫大地,誰主沉浮”的豪邁。而楊開慧,這位被毛澤東深情稱為“霞姑”的革命伴侶,其堅貞與赤誠,恰似這岳麓紅楓般耀眼。面對敵人的屠刀,她信念如磐,“丹心如故”,用年僅二十九歲的生命,詮釋了對愛人、對革命、對信仰至死不渝的忠誠。她的形象,早已化作一座精神的豐碑,矗立在歷史深處,激勵著后人。
毛澤東在《賀新郎·別友》中泣血“算人間知己吾和汝”,《蝶戀花·答李淑一》里悲歌“我失驕楊君失柳”。這份情,早已超脫兒女私情,化作革命史詩的壯麗絕唱,似山間云霞,絢麗高潔;如亭前紅葉,剎那永恒,在歲月的長河中,灼灼其華。
收回思緒,回眸亭外,一群年輕游客正舉手機,捕捉那楓葉在最后一縷夕光中的驚鴻。他們臉上的欣喜與專注,如追尋生命的火焰。他們歡快的笑聲,穿越山谷,與紅葉婆娑、山風輕吟交響成章,這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。
“山高路遠,志在千里。”古人的箴言穿越時空,在此回響。生命雖如朝露,然心懷信仰,便能在歲月刻下不朽。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愛情,猶如那火紅的楓葉,雖逝去,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。恰似“霜葉紅于二月花”,于逆境中綻放最烈的光彩。真正的愛,是靈魂的相依,更是使命的交融;真正的生,是向死而行的絢爛。

當古亭邂逅紅葉,當人文擁抱自然,岳麓山用它獨有的語言,吟唱著初冬的詩篇。長沙的初冬,因這抹紅霞而變得格外深刻。在這個信息奔涌、浮光掠影的今朝,我們或許更應駐足于此,汲取這份來自山水與歷史的磅礴力量:堅守信仰如岳麓之楓,一季絢爛可染透層林;珍視生命開慧之魂,斯人雖逝其志永耀塵寰。
楓紅霞影,剎那芳華,亦是永恒之光。